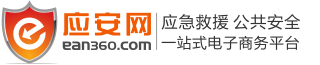《突發事件應對法》的頒布實施,對提高社會各方面依法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及時有效控制、減輕和消除突發事件引起的嚴重社會危害,最大限度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環境安全和社會秩序具有重要意義。但在該法的實施過程中,特別是非常規突發事件的應對實踐中,該法的實際應用效果受到質疑。為此,在法律實施不到兩年后,國務院就于2009年將《突發事件應對法》修訂工作納入“立法工作計劃”(國辦發[2009]2號);2010年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也有代表提交修訂該法的議案。鑒于突發事件應對是一種過程應對,過程性非常明顯,為保證每一階段應對工作有效開展,目標任務順利完成,《突發事件應對法》明確規定了每一階段應對工作的重點,并為工作任務的承擔者設置了相應的責任。因此,有必要從“責任”視角來探討《突發事件應對法》存在的問題并給出相應的建議。《突發事件應對法》責任體系相對來說比較完備,但部分具體責任規定無落實措施,影響了法律的實施效果。具體問題包括:責任規定剛性不足、不夠周延、主體缺失等。為了充分發揮《突發事件應對法》在責任追究方面的作用,有必要修改完善相關條款。
責任規定不夠剛性
立法語言的運用如何,直接關系到立法質量的高低及法律實施效果的好壞。①從立法語言分析,《突發事件應對法》有關責任設定的條款多屬“柔性條款”,剛性不夠。“可以”這類用語一般用于設定權利、職權,而“禁止”、“不得”用于設定禁止性規范,“應當”、“必須”則用于設定義務和職責。②根據這種分類,對《突發事件應對法》所有條款中這些用語的使用頻次作如下統計③:

將上表中五類法律用語的語氣強弱作個排序,應該是:“禁止”最強,其次是“不得”,“必須”、“應當”次之,“可以”最弱。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突發事件應對法》剛性不足,試作如下分析:
第一,設定禁止性規范的比例非常小,一方面說明法律剛性不足,另一方面說明這部法律最關注的是對突發事件信息的掌控,如第三十九、五十四條;對突發事件有關情況的掌握,是政府的責任,無論怎樣要求都不過分,但對于信息傳播主體而言,以如此嚴厲措辭(第五十四條預期責任規定和以之為基礎的第六十五條過去責任的規定)控制“虛假信息”,似嫌苛刻,有悖于“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因為“虛假”有時能促使“信息公開”;傳播信息不應以具備識別“虛假”信息的能力為前提。為此,建議:一、廢除第五十四條和六十五條;二、建立突發事件信息權威發布制度。
第二,“可以”是設定職權的,本法中所有涉及“可以”的相關設定都是針對政府的,所以本法中“可以”的設定應含有“權利”和“職責”雙重含義。另外,“可以”還具有“選擇自由”的含義。對政府而言,“權利”行使與否無傷大雅,如第七、四十三、四十六條有關突發事件信息的越級上報權,第十二、五十二條財產征用權和第五十二、六十條的請求支援(持)權完全可由政府自由裁量,但對于“職責”,尤其是對于突發事件應對負有主要責任的政府的職責,用“可以”來設定值得商榷,這從某種程度上講對政府這一責任主體的要求太低了。如第二十六條有關應急救援隊伍建設的規定,將政府部門應當建立專業救援隊伍的職責設定為“可以”,而將單位的職責設定為“應當”,這與本法關于責任的整體偏向是相悖的④,而且,專業應急救援隊伍的重要性至少不能以“可以”來設定⑤,這一規定極可能導致專業應急救援隊伍“應急組建”的結果,與《突發事件應對法》注重事先預防的立法目的不太協調。另外,應急救援隊伍的重要性還可以從國務院的有關規定⑥中看出。第四十九條第一款規定“自然災害、事故災難或者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后,履行統一領導職責的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下列一項或者多項應急處置措施”也有上述類似的問題,應急處置措施當然可允許選擇,實際情況不同,可采取的措施就應該不同,“或者”一詞就是表達這一含義的,但用“可以”來設定就可能會導致該選擇的措施沒選,不該選擇的卻選了,因為以“可以”來設定,就將選擇的自由交給了政府,如果政府官員決策到底采取哪些措施時避重就輕,就有可能導致因處置措施不當而延誤事件的處置與救援,這也不利于實現《突發事件應對法》“減輕和消除突發事件引起的嚴重社會危害”的立法目的。再說,《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中辦發[2009]25號)第五條也規定:“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應當問責黨政領導,這從另一側面佐證了采取適當處置措施的重要性,如此,第四十九條也應當作出修訂,至少應該用“應當”來設定,以提升這一規定的剛性程度,也從嚴要求政府在突發事件處置措施選擇上的盡其謹慎義務。為此,建議:將以“可以”設定的有關規定政府職權的條款,根據設定內容的重要程度提升至“應當”或“必須”的高度。
第三,《突發事件應對法》剛性不足,還在于法律對公權力主體的政府和私權利主體的公民、法人等同樣以“應當”來設定職責和義務。從上表可知,具體責任規定有70%都是以“應當”來設定的,而這些責任的設定有近六成是指向政府的。所以,對于政府的職責,可以用“必須”來設定其職責,而對于私權利主體,可以用“應當”來設定其義務。作出這樣區別對待的理由如下:一、對于同樣是設定職責和義務,一般要表示“一定要”、“非這樣做不可”的意思時,用“必須”;而要表示“按情理說應該”、“從人情上說應該”,適宜用“應當”。⑦也就是說,從語義學角度,“必須”比“應當”更強調行為的必要性;二、并非所有規定政府職責行為的條款都設定了相應的制裁措施,而“應當”又是個倫理概念,本身只能表現出一種道德約束力,容易在追究法律責任的執法過程中被淡化處理,導致政府責任無法落實的后果;三、以“必須”設定政府職責,體現了我黨“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的執政思想,這與“權責一致原則”是相對應的;而以“應當”來設定公民、法人等主體的義務,則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思想,按“責罰相當原則”適用法律時,有利于對私權利的保護;四、以“必須”來設定政府職責,即要求政府“不能不這樣做”,這更接近于“禁止性規范”設定效果,按照現代法治理念,政府應該按照“法有規定才可為”的理念來行政,法規定越詳細、越嚴格,政府施政才會越勤勉、越謹慎;而“應當”更多表現出的是“情理使然”,更少“禁止”的意味,公民按“法無禁止即可為”的法治理念遵照法律行事時會更多一份行動的自由。因此,有必要對“應當”和“必須”作出區分,雖然有人認為在一部法律規范當中,以“應當”和“必須”同時使用來設定職責和義務會影響法律規范的效力,⑧但鑒于政府的履職效果、盡責程度直接關系到突發事件應對的成敗,法律對政府的職責作更嚴格、特別的規定是可取的。為此,建議對《突發事件應對法》中有關政府職責的設定,根據其在突發事件應對過程中的重要程度,酌情將部分“應當”規范提升為“必須”規范。